人工智能下 未來大學應打掉“圍牆”
如果要問對這個時代最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大趨勢是什麼?可能很多人都能答上來——人工智能。面對新技術挑戰,首當其沖的正是對於未來人才培育的大學。
5月19日,國內率先設立人工智能本科專業高校之一的同濟大學建校112周年之際,在著名人工智能專家、校長陳杰的支持下,同濟大學人文學院與設計創意學院聯手舉辦“未來大學論壇”,提出“未來如何塑造大學?大學如何塑造未來?”的命題,邀請來自技術、傳媒、教育、設計、哲學等各行業專家與大學校長、學者和學生們一起,以超前的思維和創新的視野對大學在未來的各種可能性作了一次開放性的探討。
構建未來
模糊大學邊界設計改變鄉村與社區
●婁永琪(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院長)
婁永琪教授曾是一個建筑師,2004年,當他設計的學校落成時,被評價“真美、像一個園林”,婁永琪開始反思:一個學校像園林是件好事還是壞事?於是,最近十年,用他的話說就是在“拆牆”。在接受新京報專訪時,婁永琪談道:“中國大部分大學都是由圍牆圈起來的,但大學和社會的界限、和城市的界限不應該這麼明確。”
他理想中的大學是一個“道場”,有理想、有思想、有社群。各種各樣的知識、資源、人群、事件、活動的交互關系構成大學裡學生在學習,老師在教學和研究的生態系統。在這個生態系統中,每個人學習和成長的軌跡都可以不一樣。他從“拆牆”談到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強調學術與實踐、設計與生活、創新與日常相融合的理念,向大家介紹了設計創意學院從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區融入、生活方式引領到創新轉化等不同領域的案例和成果,其中包括“設計豐收”和“NICE 2035”。
12年前,婁永琪教授啟動了一個叫做“設計豐收”的城鄉交互設計研究項目,並選擇上海崇明島仙橋村進行實踐,包括改造民宿、建試驗田、蔬菜大棚、體驗大棚等,形成了城鄉交互的典型案例。對於婁永琪教授來說,這個項目最大的意義在於,在行動中逐步明白中國未來的鄉村應該是什麼樣的。
“未來的鄉村振興的核心,是能否創造性地破解產業難題,催生新的社群和文化,而不能僅僅想著商業和旅游。中國要走出和片面城市化不一樣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就是城鄉交互。”今年,婁永琪提出了“設計豐收2.0”計劃,希望通過設計思維,眾籌一個以循環經濟為特征的2平方公裡的產村融合的復合社群。
此外,婁永琪教授還發起了“NICE 2035未來生活原型街區”,推動了大學和社區的融合互動。他們和四平街道合作,在社區眾籌了一系列面向2035年的實驗室。婁永琪教授表示:“大學是年輕人才和思想、研發集聚的地方,應該主動把這部分資源外溢到社區,將社區從城市創新的終端變成源頭。”
婁永琪教授談到學院陳永群老師主持的一次研究,一位居住在上海弄堂幾十年的居民因為空間狹小,將刷牙的水斗裝到了窗外,於是每天刷牙都是“推開窗,邊刷牙,邊看風景”。“這個場景非常美,這種設計是被生活倒逼出來的。社區中人們的生活智慧,是創意設計的寶貴來源。”說到城市更新,婁永琪教授補充說:“為什麼很多這樣的項目會死掉?因為往往隻設計了物質空間,沒有設計它的魂。如果你不設計業態、運營和管理,而隻設計它的外觀,它怎麼可能活呢?”
無論是設計豐收,還是NICE 2035,婁永琪和他的團隊想要做的,是為這個世界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對話未來
人文科學不能失去介入技術生活世界的能力
●孫周興(同濟大學歐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
新京報:你為何要發起這次“未來大學論壇”?
孫周興:之所以要發起這個論壇,是因為技術工業加速發展,大學和社會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嚴峻。說實話,討論未來是有風險的,因為未來還未來。但人本質上是可能性的動物,是向未來開放的,是在對未來的籌劃中展開生活的。所以我們還必須進行這樣的討論。
新京報:隨著你在演講中提及的“人類世”的開始,技術發展愈來愈快,人類將更多地轉向非標准化的、機器無法完成的工作。在你看來,是不是已經出現了技術“倒逼”大學改革的情況?
孫周興:地質學家和哲學家把1945年標識為“人類世”(Anthropocene)的開始。所謂“人類世”意味著技術統治地位的確立,人類成為一種影響地球存在的力量。以我的理解,也意味著“自然人類文明”向“技術人類文明”的轉變和過渡。大學和一般而言的教育制度是為自然人類文明而設的,對應於自然人類文明的知識形態,而未能對已經形成的技術生活世界作出及時有效的反應。
大學當然也在改變自己,但也經常成為一種僵化的和保守的力量﹔面對現代技術的加速進程,今日大學學科建制、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變得不合時宜。這雖是全球普遍現象,但恐怕在我們這兒是最明顯的。比如我所在的人文科學,好像永遠是文史哲三門,不管世界如何變化,我們都可以躲起來緬懷過去,虛構歷史上的美好時代。
人文科學如果失去了介入當今技術生活世界的能力和責任,它不被邊緣化才是怪事一樁了。
現在新技術咄咄逼人,確實是形成了一種倒逼之勢。我曾經說過,今天的大學可能會面臨這樣的窘境:一些專業的學生被招進大學裡讀書,四年畢業后發現這個行業已經消失了。這聽起來像開玩笑,但顯然不全是笑話。
新京報:你在講座中提到,人工智能對人文科學的影響是最突出的,在未來時代裡,數碼知識與人文科學的關系將變得更為緊張,能具體展開說說嗎?未來人文科學的教育應該是怎樣的方向?
孫周興:今天以互聯網技術和大數據技術為標識的“數碼知識”已經成為主流的知識形態,而且必將對藝術人文科學造成擠壓和沖擊。具體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原本屬於人文科學的一些領域被技術化的數碼知識所佔領,比如學術翻譯,恐怕很快會被機器翻譯所取代,又比如古文獻整理,將很快不再需要自然人類來做了﹔二是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和表達方式,也將越來越技術化,近世社會科學的興起本來就是這方面的表現﹔三是人文科學學術研究的制度體系越來越被技術所規整和統轄,今天全球大學和研究機構日益嚴密和嚴苛的量化管理,已經危及人文科學的生存。
至於未來人文教育的方向,我的一個猜度性的說法是,它將致力於體驗-創意-游戲-共享,其基本任務是技術人類生活世界經驗的重建。
新京報:你還談到,不可數碼化或難以數碼化的人文科學在未來有可能發揮其別具一格的作用,哪些屬於不可數碼化或難以被數碼化的人文科學?
孫周興:人類的想象和創造在“普遍數理”之外,屬於無法被完全形式化和數碼化的藝術人文領域。這正是藝術人文科學的未來意義所在。
我不否認藝術人文科學面臨的挑戰,我也知道在未來的技術統治時代裡,藝術人文科學是難以與現代技術相抗衡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輕言放棄,相反,為了抵抗技術風險和保衛個體自由,為了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文明狀態,藝術人文科學可能是一個更重要的著力點,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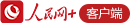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